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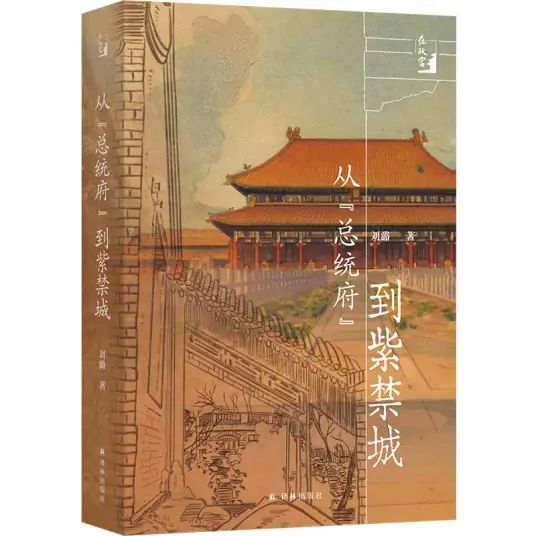
《从“总统府”到紫禁城》刘潞著 译林出版社
这是故宫学者刘潞的一部深情回忆录,既回溯个人生命轨迹,也串联起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上编聚焦作者的早年经历,以孩童视角捕捉了“总统府”里的生活片段与时代印记。下编则以亲历者视角揭开故宫工作的神秘面纱——文物修复的匠心、宫廷历史的考据,展览策划的细节。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在海外博物馆追寻故宫遗迹的见闻和中国文物流失的隐秘脉络。
我和组里同事逐一将前殿的文物擦拭完毕,随后通过小平门,经穿堂子来到后殿,也就是皇帝的寝宫。后殿共五间,中间一大间靠北墙的,是一张与北墙长度相近的宝座床。床中间有三屉紫檀炕几,上面陈有一座英国钟表。炕几两侧是供皇帝和后妃坐时使用的锦缎靠背和迎手。北墙上一幅巨大的书法贴落——宫内称贴在墙上的书画作品为贴落——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吸引我的地方,并非书法的精妙,而是落款“臣潘祖荫敬书”这几个字。这潘祖荫,不就是当年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时,从热河行宫返京后主编《治平宝鉴》一书,以历史上的太后临朝,劝进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的那个大臣吗?那时我不知道潘祖荫还是晚清的书法家,只是认为他劝进有功,其书法方可制成贴落贴于皇帝理政之处。看来,垂帘听政的历史不止于前殿东暖阁,寝宫中也有遗迹。
寝宫东稍间,是皇帝真正的卧室。沿南窗是一铺炕,炕上除了明黄缎铺垫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红漆嵌罗甸的大炕几,色彩艳丽,十分抢眼。靠北墙才是皇帝就寝的带有花罩幔帐的大炕。花罩上悬挂“又日新”大匾。不知为何,幔帐并非明黄缎,而是海蓝缎,可能是因为海蓝色有助于睡眠?帐内靠墙一侧挂了一排香荷包,应是为了散香助眠。稍间东墙挂有青金漆底嵌博古挂屏,其下沿墙放一张紫檀条案,上设两盏镂空珐琅高灯,一看便知是乾隆朝之物。两灯间摆放一座英国钟表。
组内成员均被分配在寝宫各角落,我的岗位在东稍间南炕旁。等了好一会儿,外间传来说话声,大家均想,这是英女王来了。转头一看,却是一二十位中外人士,其中一位自称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他跟我们说,这些人是使馆的。他们都站在后殿中间的宝座床旁,站在前排的,是两三位着长裙的女士。很快,女王进殿了。我还没看清女王,却见那两三位长裙女士提起裙子半蹲下去,向女王行礼。我很吃惊,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在行屈膝礼!过去仅在电影中见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现实中的屈膝礼,印象极为深刻。英女王身着红色大衣,头戴红色礼帽,手挎黑色小包,在于坚副院长和翻译的陪同下走进我所在的皇帝卧室。我像看电影一般看着眼前这位伊丽莎白二世:她个头不高,面容端庄平静,但感觉相当严肃。于院长是如何向女王介绍这寝宫的,我完全没有注意。当然,我当时也不知道跟在女王后面的那位瘦高的英国男人,就是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这时,组内养心殿的专门管理员陆成兰打开了御榻西侧的一扇小门,展示了一下皇帝如厕用的马桶。我看到女王的嘴角稍稍有些上扬。这是她进殿后我第一次见到她表情的变化。嘴角微微上扬时,不知她想到了什么。
回到组里,我见到了在漱芳斋接待女王看钟表的刘月芳,我问她此前的情形。刘月芳说,英女王对钟表可感兴趣了,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对每件钟表都认真仔细地看了个够。于是,我建议道:“月芳,你写篇文章吧!”后来,她写了一篇《英国女王在故宫观赏英国古代钟表》,发表在1987年《紫禁城》杂志第二期上。此处我摘抄一段:“贵宾们见到这些金光灿灿、造型奇特、制作精良的钟表,十分高兴。这些钟表均由机械动力控制人物、飞禽、走兽、转花、流水等装置,并能奏出乐曲。主人特意将一座‘铜镀金珐琅乐钟’上弦,立即响起了动听的乐曲。女王戴上眼镜,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一边仔细观赏,感到格外亲切。这是一座四周镶嵌有古代罗马故事珐琅画的音乐钟,表盘上有能显示时分秒、阳历和阴历,以及能变换六首英国乐曲的五组指针,是英国钟表匠1781年在伦敦制造的。女王又观赏了‘铜镀金转水法马驮钟’。钟的造型为一匹在彩蝶花丛中奔跑的铜镀金骏马。马背上有两个意大利小丑,举着带有时分秒和阴历及阳历指针的表。马下有一神秘洞窟,窟中有一群小人在台上表演。女王仔细看着钟表上的每一部分,兴趣盎然。殿堂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呈现出一片欢快活跃的气氛。”
我从刘月芳的文章里感受到,英女王观赏英国钟表远比参观养心殿寝宫时的兴致更高。更为难得的是,《紫禁城》杂志在刊发此文时,还配有故宫摄影师胡锤拍摄的女王与菲利普亲王观赏钟表的两幅照片,女王那幅正是文中描写的仔细观赏的场景,亲王那幅则十分生动:他身体前倾,探着头且微张着嘴唇,有如一个顽童,要把这来自英国的神秘、陌生之物记在心中。十五年后,我到英国访学,参观了女王的宫殿白金汉宫后,才理解了此时菲利普亲王的表情与肢体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