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终身不婚,隐世而居,一生与山为伴,只为自己写作,《活山》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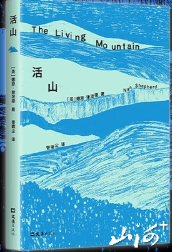
娜恩·谢泼德是大山的终身游客:她吃野果、饮河水,在湖里游泳、在山腰入眠;清晨醒来,知更鸟的爪子搭在她赤裸的胳膊上;有些时候,是野鹿吃草时的呼吸把她唤醒。
这是一曲献给大山的经典颂歌,一本捕捉流水、雪花、鹿鸣的风土故事集,更是一次通往存在的旅途,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感官实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和外在世界之间能产生多少微妙的联系:对山的生命体察得越深,对自己的了解就越深入。
没体验过夜宿山中的人,不足以称其为真正理解大山。滑入梦乡的过程中,大脑会趋于平静,身体渐渐融化,只剩下知觉尚在运转。思绪、欲望、记忆一律停止,整个人就这么沉浸在与有形世界的深入接触之中。
没体验过夜宿山中的人,不足以称其为真正理解大山。滑入梦乡的过程中,大脑会趋于平静,身体渐渐融化,只剩下知觉尚在运转。思绪、欲望、记忆一律停止,整个人就这么沉浸在与有形世界的深入接触之中。
入睡前这些静默感知的瞬间,是一天中最有价值的时刻之一。卸下所有的执着,我和天地之间再无一物阻隔。仲夏时分,午夜早已消逝,北面的光却依然闪亮。放眼望去,天光倾泻在穹顶下默然耸立的群山,它们的棱角变得更加清晰,直到其中柔软一些的线条渐渐变得虚幻,仿佛只剩下了光芒本身。在离开地球上所有其他的地方之后,光依然徘徊在这片高原的深夜深处。看着它,大脑也变得明亮而炽热,直到光芒慢慢收敛,方才遁入深沉宁静的睡眠。
日间的睡眠也很不错。日头最盛的时候大大方方躺在山间的阳光里,睡睡醒醒,补上一个清晨早起的回笼觉:这是生活中最惬意的奢侈享受之一。在山上入睡,醒来就能收获美妙。从睡眠的一片空白里回过神,在陡崖边的隘谷里睁开眼,由于忘了自己身处何方,不禁有些迷茫;在这个时候,你会重新找回平日里难以品味的原始的惊奇感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普遍经验(跟我平时的睡眠相比自然是不寻常的),但假如是在户外入睡,也许是因为比平常的睡眠更深沉,我在醒来时总是处于完全放空的状态。虽然用不了多久又会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但在那个受惊的时刻,熟悉的地方会突然焕发出新的容貌,仿佛我此前从未见过一样。
这样的睡眠可能只会持续几分钟,但即便只有一分钟,也足以解开记忆的锁扣。我有一个天马行空的猜想:也许山里的某位幽灵或是化身意图吸走我的意识,好让我能够在放下一切的空白状态下见识到最真实的大山,而这种赤裸裸的恐惧感在其他条件下难以企及。我不会把感觉归因于大山本身,但我确实没在其他任何时刻有过如此沉入生命的体验。这一刻,自我彻底释放。正因可遇而不可求,这种经历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凌晨四点出发,就能享受好几个小时这样的静谧时光,甚至还能有机会在山顶入睡。身体随着登山的节奏灵活运转,在进食后的悠闲里得到放松。你会感到无比宁静,像石头一样,深深地沉入静止状态。脚下的土壤不再是大地的一部分。假如睡意在此刻降临也毫不奇怪,它的到来就和日升日落一般自然。过了一会儿你睁开眼,不再像一块石头,不再与大地融为一体;目光牵引着你感知身边的一切,直到醒来以前你都是它的一部分。你曾身处其中,而如今这已经过去。
不过,我也曾经在本不会选择入睡的地方睡着过。当时我们在布雷里厄赫山,地平线蒙上了一层薄雾,平淡的景色毫无生机、趣味寡淡。因此我们就在山顶的另一边趴着,尽最大勇气靠近边缘,身体牢牢贴近地面,朝下望向布若翰冰斗。河水满溢,瀑布的喧哗声随处可闻。我们看着飞流直下的瀑布一路倾泻,砸落在岩石上。在远低于我们的山谷谷底,鹿群正在觅食,像是一个个缓慢移动的斑点。我们就这么看着它们走来走去。随后太阳露脸,洒下暖洋洋的光,眼前的动作和声音变得令人昏昏欲睡。再然后,我猛地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正望着一堵深色石墙,而山底远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估计,从山顶到河床实际上大概有两千英尺的距离,到山腰那片鹿群觅食的洼地大概不超过一千英尺;但在睁开眼的那“惊魂一瞥”间,所有的思考和记忆都尚未回归,只剩纯粹的感觉,于是眼前的陡降便显得极度突然。我深呼一口气,说了句:“原来是布若翰!”翻过身,从山边缓缓后退,然后站了起来。就在刚才,我曾凝视深渊。
如果说无知无觉是白天睡倒在山间的恩赐,那么夜空下最美妙的就是轻浅的睡眠。我特别喜欢这种浅淡的状态,能让我在回归意识表层和再次沉入睡眠之间不断循环,只静静看着,不为思虑困扰,就这样体验着感官的简单与明澈。早至五月、晚至十月的第一周,我都在野外露宿过。这段时间里,在我们古怪而错乱的气候条件下,通常也会有几次光芒四射的好天气。
某个绸缎般温柔的十月夜,我躺在星空下,看着一轮明月直至凌晨才缓缓升起。在光滑而柔软的破晓时分,山脉犹如流转的湖水,连绵起伏。这一夜犹如完全拜巫术所赐,教人为所有充满魅力的故事赞叹不已;苏格兰如此努力地驳斥巫术的存在,却从未成功。对此,我毫不讶异。任何一个凌晨四五点还待在户外的人遇到这样的一个清晨,都会开始迷糊得犯拼写错误;在被窝里睡到八点的人才不会想到“仙境”“迷人”或是“魅力”这种词。找个足够温暖的十月尝试夜宿野外,体验一次晨曦与月光交织的黎明,你就会明白我说得没错。到时候,你也会中拼写错误的迷咒。
我不喜欢魅惑,因为它在世界这一重现实与自我这一重现实之间插入了某些东西,虽说自我现实早已被许多层虚假幻象和社会习俗掩盖;但正是这两种现实的融合,保护着生命免于腐坏。所以,让我们摆脱这些迷咒吧!
我大部分的野外露宿都发生在简单的夏日夜晚。我喜欢在这样的夜晚不断醒来,因为彼时的世界实在太美,也因为野生鸟兽会毫无戒备地靠近睡着的人。不过,如何醒来也是一门艺术。头脑必须完全清醒,睁开双眼时身体不能有分毫移动。某个白天我猛地惊醒,发现有一只习惯从手中啄食的小黑鸟正在腿上走来走去。他挤出一种诡异嘶哑的轻笑声,想要向我讨食,不过声音实在太过低沉,没能穿透我的睡眠。还有一次,一只苍头燕雀碰了碰我的胸膛。这两次我都睡得很浅,立马感受到了来访者的动作,并及时醒来,看到了它们匆忙飞走的样子。要是我没笨到跳起来就好了!但毕竟我的睡眠被打破了呀。不,必须得是自然而然地醒来:原本闭着的眼睛现在睁开了,仅此而已,再不能有其他动作。离我十码外的地方,一只马鹿正在晨曦中觅食,他无声地移动着,整个世界完全静止。我也静止了。我是静止了吧?还是说我移动过?他抬起头,抽了抽鼻子,随后我们四目相对。我为什么会蠢到让他看见我的眼睛?他跑开了。不过没走太远。他一边跑一边看,又回头看了看我。这一次我没有望他。不一会儿,他低下头,放下心来继续觅食了。
有时我会在黎明时分从梦海浮上水面,看到一只狍子,在他给我的意识留下清晰印象之前,我会再度陷入沉睡。虽然我不能在法庭上为此宣誓,但这一瞥依然带来了一阵相当真实的幻觉。那天早晨彻底清醒之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晚些时候,这个画面才开始在我大脑边缘浮现——不过,那只狍子是不是我在做梦时梦到的呢?——由于无法确定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个想法困扰了我很久。
在我睡觉的地方下面,木栅里可能到处都是雀鸟。有一次,我睁开眼数了数,竟然有二十只。也可能是山雀,一如既往地迈着有趣的步子跳来跳去。山雀家族里把这一项做到极致的是其中最罕见的小凤头山雀,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它四处炫耀,一会儿蹦到前面,一会儿跳回后面,一会儿又跑到一边,每个姿势维持片刻,立马转移到高处或低处的树枝上继续:活脱脱一个精致的模特!
有些时候,最先醒来的是耳朵。鹬发出有节奏的啼鸣。我从睡袋里坐起身,在天空里寻找它们俯冲而下的可爱身影。有时天还是太黑(即便是在苏格兰的盛夏),看不清它们的飞翔轨迹,只有飞速下降的声音尽在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