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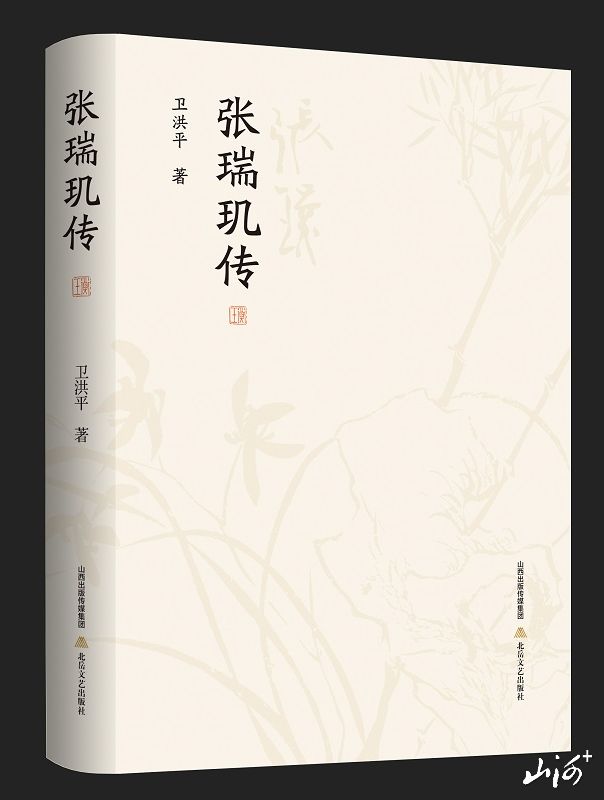
《张瑞玑传》卫洪平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年春天,我在太原参加了王春林文学评论的研讨会,就和几个朋友开车去了大同。一次文友相聚,与卫洪平先生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诚朴的一个读书人。
2023年秋天,又去山西,是到一个老友的老家,探望他的老父母。洪平消息灵通,来宾馆喝茶聊天,送我一本他新出的《张瑞玑先生年谱》。这是一本很重很厚的书,文笔也很好。我读书不快也不慢,在山西的几天里,一有空我就捧起来,断断续续,竟然也就翻完了。在新写的《消息》里,我还用了一些张瑞玑先生的事迹。
一个诚朴的读书人,三十年来一直埋着头,一点一滴搜集张瑞玑的种种资料;公务之余,熬油点灯,耐着性子,耐住寂寞,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琢磨成了这么一部厚厚的大年谱。同为文字劳动者,洪平的艰苦,我也实实在在尝过。
如此又过了两年,他写出了《张瑞玑传》。其中的三章,叙写张瑞玑在陕为官的经历,在我主编的《美文》杂志上连载过。
从《张瑞玑先生年谱》到《张瑞玑传》,洪平对历史的深情,温润平实的笔调,以及对现实的关切,始终都是一贯的。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风骨凛然的张瑞玑,在他的笔墨下复活了。
现在,我的心里满是,为他终于完成此作的欢喜。
卫洪平先生对近代山西历史资料、山西与陕西的近代历史、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均非常熟悉,数十年积累下来成果颇丰。尤其是他为研究乡贤张瑞玑殚精竭虑,曾编辑了张氏年谱,现在又撰写出《张瑞玑传》。在书中,他展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底,不但能利用多种资料详细钩沉了张氏特立独行的一生──从清末能吏到民初国会议员,再到为各方看重的政坛要角,详述其敢作敢当对抗袁世凯、对抗地方军阀等往事,又特别注意在分析张氏思想时使用其诗歌文献,史、诗结合,字里行间饶富感情,很好地再现了谔谔一士张瑞玑的形象,读之不由让人产生共鸣。
总言之,该书是一本精心结撰之作,或可被视为管窥清末民初山西历史的一扇窗,对推进山西文史研究和中国近代人物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瑞玑(1872-1928年)字衡玉,号老衡、谁园第一主人、窟野人,清末民初山西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人。早年以宰官秘密加入同盟会,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敢到北京菜市口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敛尸,敢公开致书嘲骂袁世凯阻其窃夺临时大总统,敢铸军阀卢永祥跪状铁像任百姓踩踏唾骂十余年,敢置个人安危荣辱于度外,“骑虎”赴陕,为1919年南北议和清障……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藏书家。卫洪平先生业余研究张瑞玑达30年之久,继2020年出版《张瑞玑先生年谱》(获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后,又焚膏继晷,写出32万字的《张瑞玑传》,近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贾平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教授倾情推荐。贾平凹认为,“一个有血有肉、风骨凛然的张瑞玑,在他的笔墨下复活了”。张仲民称赞此书“再现了谔谔一士张瑞玑的形象”“对推进山西文史研究乃至中国近代人物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本报今日刊登此书后记,略有删节。
《张瑞玑先生年谱》出版后,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一些反响。
《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及中国作家网、光明网、澎湃网等做了报道。诸多师友和读者撰写书评,赋诗道贺,跟帖点赞。后又获得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人们忽然发现,近代山西还有这样一位“民国巨子”,一个风骨凛凛、大才槃槃的“奇人”!
一
《年谱》责编韩玉峰约我写传。
起初打算写一本故事类小册子,让更多读者走近张瑞玑。退了休,再写一部大传或评传。梳理脉络、构思框架时发现,故事类小册子分量太轻,远不能承载传主瑰奇壮阔的人生。应该写一部完整的传记才是。
怎么写呢?
我在学习思考中,决意遵守中国史传传统,写一部“实录”。传主天纵奇才,中年后作《像赞》自嘲:“文士之笔,辩士之口。循吏之心,酷吏之手。狂士之诗,豪士之酒。侠士之挥霍,廉士之操守。北美洲之思想,南非洲之紫首。”观其一生出处大节,无不攸关国事苍生,攸关民主共和政治理想。尤可称者,临危难而不苟,大智大勇,能进能退,绝然不同于历史上那个“事四姓十君”的“长乐老”冯道。
“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
写作中,我把戴名世《史论》中的这句话奉为圭臬。依此探寻传主参加科举,由仕清而革命,两度隐居谁园,抚松盘桓,以及经历许多重大事件——维新变法、庚子国变、清末新政、国会请愿、辛亥革命、癸丑之役、洪宪帝制、护法运动、南北议和、北京政变、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轨迹,竭力探究其“迹”和“所以迹”。
我陆续研读了范文澜、陈旭麓、章开沅、桑兵、罗志田、蒋廷黻、郭廷以、张朋园、费正清等海内外史学大家的相关著述。期能以一个较为宽广的视野,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寓宏观于微观,最大限度地复原传主所处的历史现场,复原时代风云投射在传主身上、心上的影像。
二
史学重实证,个案研究尤其如此。多年来,我在国家图书馆、国图北海古籍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博物院、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洪洞县博物馆、临猗县图书馆、平遥中学图书馆等处,查找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又查阅了1912年《临时政府公报》,1912-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公报》,打印、摘录了相关内容。逐日阅读、抄录、整理了《申报》1919年2月至6月有关张瑞玑赴陕西监视停战划界的报道和时评;参以中国民国《政府公报》、南方《军政府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益世报》、北京《公言报》(林白水任主笔)等。检索总目、阅读、摘录相关内容的有:中华书局《辛亥革命回忆录》(1至6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85年至2017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157辑),山西省政协《山西文史资料全编》(120辑)。
此外,搜读了十余种有关晋陕辛亥革命、陕西靖国军始末的重要著述。翻阅了上百种与传主有过交际的重要人物传记、年谱、日记、著述、纪念文集,这些人物包括: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钱能训、岑春煊、朱启钤、唐绍仪、唐继尧、林森、宋子文、章太炎、田桐、刘成禺、于右任、井勿幕、张凤翙、陈树藩、胡景翼、郭希仁、张季鸾、张钫、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谷如墉、景耀月、景梅九、李岐山、续西峰、南桂馨、贾景德、刘盥训、孙奂仑、赵炳麟、郭象升、吴庚、赵意空、韩坰、尚小云、俞瘦石、樊增祥、易实甫、罗瘿公、王寿彭、卢永祥等。
传主遗存的几部手稿,其哲嗣张尔公(字筱衡、小衡)裒辑的六册十二卷《谁园集》,一度被查抄,“文革”后幸得珠还。彼时尔公已殁,其生前友好为保存遗珍,与尔公长子、传主长孙祖望商量,由古旧书店一位高先生出面,作价两千元,悉数归藏到陕西省博物馆,计有:《张老衡诗稿》一册,《䍺窟野人诗稿》一册,《张瑞玑函电底稿》一包,《谁园集》六册,《谁园藏书目录》一册;另有张尔公《华夏语文通释》等手稿。尔公是西北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家,论者谓他“在商周金文研究领域与陈进宜、侯外庐、郭沫若、徐中舒、唐兰颉颃”。1980年,传主外孙王作霦教授,在陕西省博物馆文史资料库查见这批藏品,随手列了一份《先外祖父张瑞玑及先舅父张小衡稿本存陕西省博物馆清录》,总共二十九种、一百四十五册。离奇的是,当1996年陕西某好事者冒充张瑞玑后裔,炮制所谓“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闹剧落幕后,山西省图书馆组织出版《张瑞玑诗文集》,派人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前身即陕西省博物馆)查阅那批手稿,竟无踪影!七八年前我去西安,偕传主曾孙张七先生到该馆查询,无果。带着挥之不去的遗憾,离开这个素负盛名的博物馆。
张七先生陪我在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拜访了他的父亲、传主长孙、九十岁的祖望老人。老人念过教会学校,交谈时偶尔夹杂英文词汇。他在年轻时受过刺激,许多珍贵的记忆已封存心底。
幸运的是,那个傍晚,我在张七先生家中——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住宅楼——得见几种珍贵资料:
(一)两帧传主照片。一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录》中的肖像,一为做临潼知县时在华清池集体合影。另有传主发妻刘氏夫人晚年肖像。
(二)一部张尔公《先君事略》手稿,朱丝栏,六十二页。应是章太炎撰写《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用作参考的那一部。
(三)三本民国政要和各界名流吊祭传主的哀挽簿(原稿)。有黎元洪、宋子文的挽词,阎锡山的祭文,张凤翙、赵戴文的挽联,田桐、温寿泉的挽诗等。
(四)一件公函。张尔公捐献的谁园藏书一万六千七百余册“全部运省”后,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1952年5月31日所发感谢函。另有尔公应邀赴并,主持整理谁园藏书前后,有关人士写给他的书信八通。
随后,我又相继得到传主几位后裔——兰州王宪先生、北京郝伟先生、西安梁翔云女士、长春张梅女士、洪洞王素云女士——提供的口述资料和张氏宗谱。
传主的踪迹,我去寻访过的有:北京国会旧址、上海外滩“南北议和”旧址、广州大元帅府、雨花台、南京浦口火车站、陕西韩城县古城、韩城县衙大堂、临潼县骊山、河南开封贡院旧址、开封山陕甘会馆、开封书店街等;山西咨议局旧址、山西大学堂大公堂、太原首义门、太原文庙、灵石县韩信岭、乡宁县吾园、洪洞县赵城谁园、广胜寺、女娲庙、罗云山、七佛峡等。
上述种种,大都写进《张瑞玑先生年谱》了。还有不少资料,是在年谱出版后、传记写作过程中陆续发现的。AI时代,我学会用强大的搜索引擎,在国内权威的学术数据库中追踪遨游。线上线下,也得到王开学、孙灏东、赵中亚诸君的热忱相助。
传主是杰出的诗人,兼擅书画,“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腕底风云,苍雄奇恣,笔墨中见才情,见智慧,见风骨,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涵泳其间,时而眼前一亮,陶然于以诗证史、以诗明史的乐趣。
缺憾自然是有的。最大的缺憾,要数前面提到的传主几部手稿,怎么就“失踪”了?再者,数十年“上穷碧落下黄泉”,未能发现传主与“五四”相关的任何记载,生活方面的资料,也少得可怜。
只能付之阙如了。
三
我年轻时喜欢读人物传记,至今仍有兴致。多年来,我对自己偏爱的诸多中外传记经典,一读再读,如鱼饮水。自知在谋篇、布局、叙事、剪裁、语言、笔调、审美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心得。等到自己要动手写一部人物传记了,仍不免发怵。写作过程艰苦备尝,仿佛眼前横着一座大山,沟壑纵横,奇峰迭出。常自念叨:“这样写行吗?”想到贾平凹先生年前来山西采风,我送过一册《张瑞玑先生年谱》,他看后表示欣赏;便把写了半截的传稿,摘出传主在陕西为官、参加辛亥革命的章节,托朋友转去,请他看看。承贾老师青睐,很快就在他主编的《美文》上,以“长篇散文连载”登了三期,每期一万多字。这使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接下来,写得也苦。
尤其是1919年南北议和,张瑞玑受双方总代表公推,赴陕西监视停战划界,由此进入其政治生涯的高峰那一段。当其时也,北京政府与南方军政府开启的南北议和,才谈到第四回,便因陕西战事而陷于停顿。齐集上海的双方代表,能否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国人翘盼的南北议和,能否继续开议?《申报》时评称:“和议之进行与否,悬于陕事之手;陕事之能了与否,悬于张瑞玑之手。”
传主此行,关系极大!
而陕西那边的情形,极为错综复杂。一则,“南北主客驻陕军十三万,集八省之兵,合数省之匪,星罗棋布于关中一隅,纵卸甲坐食,秦已不堪。……此电入览,八百万呼吁之声隐隐纸上矣”!两军相接,随时都有引发战事的可能。二则,兵匪不分的问题十分严重。三则,对立的双方——一方是陕西督军陈树藩,一方是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南方军政府亦任命为“陕西督军”)——与张瑞玑都是老朋友;北京政府派去的援陕总司令、奉系军阀许兰洲,入关前就有窃据陕西督军宝座的图谋。在如此严峻、复杂、危急、紧迫的局势下,传主“骑虎”西行,虽说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然欲不辱使命,又谈何容易!
梳理这段历史,我深感力不从心,担心自己能否爬过去。
大哥建民是散文家,多年研究孙犁,有闲静之气。他在电话里说:“先写完,写完再说。”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也想到贾平凹老师谈陕西作家群的那句话:“对自己狠。”说起来,我一向对自己也算狠的,每遇重要关节,会生出一股蛮劲来。狠点,再狠点,哪怕写完了病一场!
吊诡的是,新冠疫情头几年,我侥幸躲过了,后来却阳了又阳。书稿一拖再拖,到2024年的最后一天,凌晨两点才杀青。
总算趔趄着爬过来了。
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考证、补充、深入的过程。譬如传主名作《谁园记》里有一句:“昔李廌记洛阳名园一十九。”李廌系李格非之误。传主博古通今,怎么会错?早些年,我看到明代毛晋有个著名的刻本——汲古阁本《津逮秘书》——就弄错了,那里面收有《洛阳名园记》,将作者误植为“宋华州李廌撰”。谁园十万卷书楼该有汲古阁本《津逮秘书》吧?我查了山西省图书馆藏的《谁园书目》,没有。但我推测,《谁园记》里这一处“硬伤”,该出自三百年前的汲古阁,《年谱》中便说:“谱主藏书极富,误当本此。”两年前,我在平遥中学发现了钤着“谁园”“谁园藏书”“谁园十万卷书楼”“赵城张氏藏书”“老衡鉴定”“䍺窟野人”等藏书印的五千多册谁园藏书,里面果然有汲古阁本《津逮秘书》。这回写传记,就把“误当本此”改作“误即本此”了。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先生,应出版社邀请,拂暑审读了全部书稿。我以前读过张著《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其中《南桂馨与刘师培》《南桂馨与阎锡山》两篇,抉微发幽,揭出背后的真相,让人佩服。审稿过程中,张老师的严谨、细致、谦厚、热忱,以及不疑处有疑的学人风范,益我良多。
出书在即,贾平凹老师慨予推荐,感何如之。
“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钱乘旦语)
“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就是挑战我们的智商,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本事通过这些片面的、零碎的资料复原出真实的历史。”(葛剑雄语)
如果从1996年撰写长文《张瑞玑其人》(发表于1997年3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算起,我业余研究张瑞玑三十年了。我把三十年来搜集的历史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期能写出历史现场的张瑞玑,写出在我心中已然复活的张瑞玑,向读者呈现出他那一身的骨气、豪气、奇气、清气和逸气。
我尽了全力。
我用文字给他塑了一尊雕像。在这过程中,也渐渐体验到聚精之后真能会神的那样一种境界。
至于这尊雕像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今天塑这样一尊雕像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就只有听候各位方家和读者诸君的评断了。

